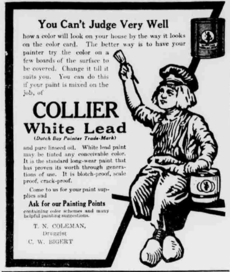有毒重金属
编辑有毒重金属是指一种相对致密的金属或者非金属,尤其是在环境领域中因其潜在毒性而闻名。[1] [2] 有毒重金属这一名词通常是用来指镉、汞、铅、砷这四种元素,它们都位列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公共关注的十大主要化学品清单中。除此之外,它还包括有其他重金属:锰、铬、钴、镍、铜、锌、硒、银、锑和铊。
重金属在地球上是自然存在的,因人类活动而富集,并且可以通过吸入、进食以及人工处理的手段进入到植物、动物和人体组织当中。然后,它们可以通过干扰和与细胞重要成分进行结合进而影响其功能。砷、汞、铅的毒性作用早在古代就已经为人所知,但对某些重金属毒性的系统研究似乎仅始于1868年。对人类而言,重金属中毒通常通过服用螯合剂来治疗。一些被认为是有毒重金属的元素其实对人体健康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所需含量很小。
1 污染来源编辑
重金属在地球上自然存在,并且由于人类活动和某些情况下的地球化学过程(如其在泥炭土中积累并在农业排水时释放)而发生富集。[3] 常见来源有:采矿和工业废物、车辆排放、铅酸电池、肥料、油漆、处理过的木材,老化的供水基础设施、 漂浮在世界范围海洋中的塑料微粒等等。[4] 儿童玩具中的砷、镉和铅的含量很可能超过了监管标准。其中铅可以用作玩具的稳定剂、增色剂或抗腐蚀剂。镉有时被用作稳定剂,或增加玩具的质量和光泽,而砷被认为是与染料有关。[5] 长期饮用非法蒸馏酒精可能会导致砷或铅中毒,中毒来源是在焊接蒸馏装置时所使用到的砷、铅元素。谷物和饲料储备过程中使用的鼠药也可能是砷的另一个来源。[6]
铅是最常见的重金属污染物。[7] 作为四乙基铅(CH3CH2)4Pb的组成成分,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被广泛应用在汽油产业中。[8] 据估计,工业化社会水环境中的铅含量是工业化之前的两到三倍。[9] 1996年,尽管北美含铅汽油的使用基本上已逐步被淘汰,但在此前修建的道路旁的土壤中的铅浓度含量仍然很高。铅(来自枪支中使用的叠氮化铅或史帝芬酸铅)在枪支训练场中逐渐积累,污染当地环境,使靶场员工面临铅中毒的风险中。[10]
2 进入途径编辑
重金属通过空气吸入、进食和人工处理这些方式进入到植物、动物以及人体组织内。机动车尾气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包括砷、镉、钴、镍、铅、锑、钒、锌、铂、钯和铑。[11] 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中浸出的重金属可以污染水源(地下水、湖泊、溪流和河流);酸雨会释放土壤中的重金属,从而加剧这一过程。[12] 优先流动路径(大空隙)以及溶解的有机物的存在可以促进重金属在土壤内的转移。[13] 植物通过吸收水分接触重金属;动物食用这些植物;摄入植物和动物类食物是人体中重金属的最大来源。[14] 通过皮肤的接触吸收,例如通过接触土壤,或含有金属的玩具和珠宝,[15] 是重金属污染的另一个潜在来源。[16] 这些有毒重金属很难被代谢,可在生物有机体中发生生物积累。[17]
3 危害编辑
重金属“可以与细胞的关键组分结合,如结构蛋白、酶以及核酸,并影响它们的功能”。[18] 根据金属或金属化合物的种类以及它们剂量的不同,症状和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通常来说,长期接触有毒重金属可能会致癌,并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以及循环系统。对于人类而言,接触这些“传统”有毒重金属、铬(另一种有毒重金属)[19] 或砷(非金属)所带来的相关典型症状如下表所示。[20]
| 元素 | 短期接触 通常一天或不到一天 |
长期接触 通常几个月或几年 |
| 镉 | 肺炎(肺部炎症) | 肺癌 骨软化症(骨头软化) 蛋白尿(尿液中含有过量的蛋白质;可能伴有肾脏损伤) |
| 汞 | 腹泻 发热 呕吐 |
口腔炎(牙龈和口腔炎症) 恶心 肾病综合征(非特异性肾病) 神经衰弱(神经症) 味觉混乱(金属味) 粉红病(手脚疼痛和粉红变色) 震颤 |
| 铅 | 脑病变(脑功能障碍) 恶心 呕吐 |
贫血症 脑病 变 足下垂/手腕下垂(麻痹) 肾病(肾功能障碍) |
| 铬 | 胃肠渗血(出血) 溶血(红细胞被破坏) 急性肾功能衰竭 |
肺纤维化(肺部疤痕) 肺癌 |
| 砷 | 恶心 呕吐 腹泻 脑病 多器官效应 心律不齐 疼痛性神经病 |
糖尿病 色素减退/角化过度 癌症 |
4 历史编辑
砷、汞、铅的毒性影响早就为古人所知,但对重金属整体毒性的系统研究似乎仅始于1868年。当年,万克林(Wanklyn)和查普曼(Chapman)推测了饮用水中重金属“砷、铅、铜、锌、铁、锰”的不良影响。他们提出这方面“缺乏调查”, 并总结了“收集数据进行引证的必要性”。[21] 1884年,布莱克(Blake)描述了毒性与元素原子质量之间的明显联系。[22] 以下章节对重金属的历史做了简要阐述,内容包括“传统”有毒重金属(砷、汞、铅)和一些最近的实例(铬、镉)。
4.1 砷
砷,例如雄黄(As4S4)和雌黄(As2S3)这两种物质,早在古时候就已经为人所知。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50年-公元前24年),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23] 他曾写道,因为雄黄和雌黄矿石中散发出的烟雾的毒性会不可避免地使人的死亡,因此这些矿区中一般只雇佣奴隶。1900年,在英格兰曼彻斯特地区,被砷污染的啤酒导致6000多人中毒,据说已造成至少70人死亡。[24] 克克莱尔·卢斯(Clare Luce)——1953年至1956年期间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曾遭受砷中毒。中毒的来源可能是到她卧室天花板上含砷油漆的剥落,也可能在大使馆餐厅吃到了因为天花板油漆剥落而被砷污染的食物。[25] 截至2014年,被砷污染的地下水“仍在毒害数百万亚洲人”。[26]
4.2 汞
据报道,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死于服下了意在使他永生的水银丸。[27] 在18世纪和19世纪,汞基化合物一度被用于制造毡帽,所以短语“疯帽匠”很可能是指帽子制造商中出现的汞中毒现象(所谓的“疯帽子病”)。[28] 历史上,金汞合金(一种含汞合金)被广泛用于镀层工艺中,其结果导致了工人的大量伤亡。据估计,仅在圣艾萨克大教堂的建造过程中,就有60名工人死于主穹顶的镀层过程。[29] 20世纪50年代,由于汞通过工业排放进入到河流和沿海水域,日本几个地方爆发了甲基汞中毒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水俣和新泻两地的中毒事件。仅在水俣这一个地方,就有600多人死于后来被称为水俣病的疾病。超过21000人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并且其中近3000人被证明患有该疾病。在22个记录在案的案例中,食用了受污染鱼类的孕妇均表现出轻微的中毒症状或压无症状,但却产下了患有严重发育障碍的婴儿。[30] 自工业革命以来,许多近海水域的汞含量增加了两倍,尤其是冰岛和南极洲附近附近。[31]
4.3 铅
铅的副作用为古人所熟知。公元前2世纪,希腊植物学家尼坎德(Nicander)描述了铅中毒人群中的腹绞痛和瘫痪症状。[32] 狄奥斯科里迪斯——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医生,[33] 曾写道,铅“让人失去理智”。公元前500年到公元300年,铅被广泛用于罗马水渠。[34] 据尤利乌斯·凯撒的工程师维特鲁维阐述(Vitruvius):“陶管中的水比铅管中的水更有益健康。管道中的铅似乎会使水变得有害,因为铅管当中产生了白铅,据说这是对人体有害的。”[35] 在中国蒙古国时期(公元1271-1368年),云南地区炼银造成的铅污染比现代采矿活动造成的污染水平高出近四倍。[36] 17世纪和18世纪,德文郡的人们患有一种称为德文腹痛的疾病;后来被发现是由于人们饮用了被铅污染的苹果酒。2013年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143000人因铅中毒而死亡,并且每年“贡献”600000名智力障碍儿童的新病例。[37] 在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饮用水中的铅污染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是个问题。污染源归因于“用于向居民供水的含铅、铁管道腐蚀”。[38] 2015年,据报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东北部的饮用水铅含量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的50倍以上。污染源归因于“破旧的饮用水基础设施,包括铅连接管道、报废的聚氯乙烯管道和家庭管道”。[39]
4.4 铬
铬(III)化合物和金属铬单质被认为对健康无害,而铬(VI)的毒性和致癌性最早从19世纪晚期就已被人们所知了。[39] 1890年,纽曼(Newman)报道了铬酸盐染料公司工人患癌风险升高的现象。[4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报道称飞机厂工人患有铬酸盐引起的皮炎。[41] 1963年,英国60名汽车工厂工人爆发了皮炎,患病范围从红斑到渗出性湿疹。工人们用湿砂纸打磨了用于车身的铬酸盐底漆。[42] 2011年8月8日,铬从澳大利亚奥里卡炸药厂泄露出来。该工厂多达20名工人以及斯托克顿附近的70户家庭也暴露在外。该镇在事故发生后三天才得到通知,此事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公众争议,奥里卡因淡化泄漏的程度和可能的风险而受到批评,州政府也因对此事件反应迟缓而受到抨击。[43]
4.5 镉
镉的泄露是20世纪早期的污染现象。1910年,1910年,日本天水矿业冶炼公司开始将镉作为采矿作业的副产品排入金祖川河。。周边地区的居民随后食用了镉污染的灌溉水种植的水稻,因此患上了软骨病和肾衰竭。这些症状的起因在当时尚不清楚,当时提出的可能性是“区域性或细菌性疾病或铅中毒”。[44] 1955年,镉被确定为是致病的可能原因。1961年人们确定了镉的来源与该地区的采矿作业直接相关。[45] 22010年2月,人们在沃尔玛独家发售的米莉·赛勒斯(Miley Cyrus)珠宝中发现了镉,但沃尔玛依旧继续出售这些珠宝。直到5月美联社组织的秘密测试证实了最初的结果,沃尔玛才对这些珠宝的停止销售。[46] 2010年6月,在麦当劳餐厅出售的电影《永远的史莱克》的宣传酒杯上使用的油漆中发现了镉,该事件导致1200万只玻璃杯被召回。[47]
5 修复编辑
对人类来说,重金属中毒通常是使用螯合剂来进行治疗。[48]这些螯合剂属于化学化合物,如CaNa2EDTA(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钙 ),可将重金属转化为化学惰性形式,使得其在没有进一步与身体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被排出体外。螯合物并非没有副作用,它也能去除人体内的有益金属。因此,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有时也会同时服用。[49]
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可以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技术进行修复,包括有:隔离、固定、降低毒性、物理分离、萃取等方法。隔离包括使用覆盖、薄膜或地下屏障来隔离被污染的土壤。固定化的目的是改变土壤的性质,从而阻碍污染物的移动。降低毒性指通过化学或生物手段将有毒重金属离子氧化或还原成毒性较小或可转移的形式。物理分离包括去除被污染的土壤和通过机械手段分离金属污染物。萃取是一种利用化学物质,通过高温挥发或者电解的手段从土壤中提取污染物的现场或场外的过程。使用的过程将根据污染物和现场的特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50]
6 利益编辑
参考文献
- [1]
^Srivastava & Goyal 2010, p. 2.
- [2]
^Brathwaite & Rabone 1985, p. 363.
- [3]
^Qureshi, Shabnam; Richards, Brian K.; McBride, Murray B.; Baveye, Philippe; Steenhuis, Tammo S. (2003). "Temperature and Microbial Activity Effects on Trace Element Leaching from Metalliferous Pea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 Quality. 32 (6): 2067. doi:10.2134/jeq2003.2067..
- [4]
^Howell et al. 2012; Cole et al. 2011, pp. 2589‒2590.
- [5]
^Finch, Hillyer & Leopold 2015, pp. 849–850.
- [6]
^Aggrawal 2014, p. 680.
- [7]
^Di Maio 2001, p. 527.
- [8]
^Lovei 1998, p. 15.
- [9]
^Perry & Vanderklein 1996, p. 336.
- [10]
^Houlton 2014, p. 50.
- [11]
^Balasubramanian, He & Wang 2009, p. 476.
- [12]
^Worsztynowicz & Mill 1995, p. 361.
- [13]
^Camobreco, Vincent J.; Richards, Brian K.; Steenhuis, Tammo S.; Peverly, John H.; McBride, Murray B. (November 1996). "Movement of heavy metals through undisturbed and homogenized soil columns". Soil Science. 161 (11): 740–750. doi:10.1097/00010694-199611000-00003..
- [14]
^Radojevic & Bashkin 1999, p. 406.
- [15]
^Guney, Mert; Zagury, Gerald J. (4 January 2014). "Bioaccessibility of As, Cd, Cu, Ni, Pb, and Sb in Toys and Low-Cost Jewelry".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8 (2): 1238–1246. Bibcode:2014EnST...48.1238G. doi:10.1021/es4036122. PMID 24345102..
- [16]
^Qu et al. 2014, p. 144.
- [17]
^Pezzarossa, Gorini & Petruzelli 2011, p. 94.
- [18]
^Lanids, Sofield & Yu 2000, p. 269.
- [19]
^Neilen & Marvin 2008, p. 10.
- [20]
^Afal & Wiener 2014.
- [21]
^Wanklyn & Chapman 1868, pp. 73–8; Cameron 1871, p. 484.
- [22]
^Blake 1884.
- [23]
^Dueck 2000, pp. 1–3, 46, 53.
- [24]
^Dyer 2009.
- [25]
^Whorton 2011, p. 356.
- [26]
^Notman 2014.
- [27]
^Zhao, Zhu & Sui 2006.
- [28]
^Waldron 1983.
- [29]
^Emsely 2011, p. 326.
- [30]
^Davidson, Myers & Weiss 2004, p. 1025.
- [31]
^New Scientist August 2014, p. 4.
- [32]
^Pearce 2007; Needleman 2004.
- [33]
^Rogers 2000, p. 41.
- [34]
^Gilbert & Weiss 2006.
- [35]
^Prioreschi 1998, p. 279.
- [36]
^Hillman et al. 2015, pp. 3353–3354.
- [3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
- [38]
^Torrice 2016.
- [39]
^Harvey, Handley & Taylor 2015.
- [40]
^Newman 1890.
- [41]
^Haines & Nieboer 1988, p. 504.
- [4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74, p. 68.
- [43]
^Tovey 2011; Jones 2011; O'Brien & Aston.
- [44]
^Vallero & Letcher 2013, p. 240.
- [45]
^Vallero & Letcher 2013, pp. 239–241.
- [46]
^Pritchard 2010.
- [47]
^Mulvihill & Pritchard 2010.
- [48]
^Blann & Ahmed 2014, p. 465.
- [49]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08; National Capital Poison Center 2010.
- [50]
^Evanko & Dzombak 1997, pp. 1, 14–40.
- [51]
^Bánfalvi 2011, p. 12.
- [52]
^Chowdhury 1987.
- [53]
^Hillman et al. 2015, p. 3349.
暂无